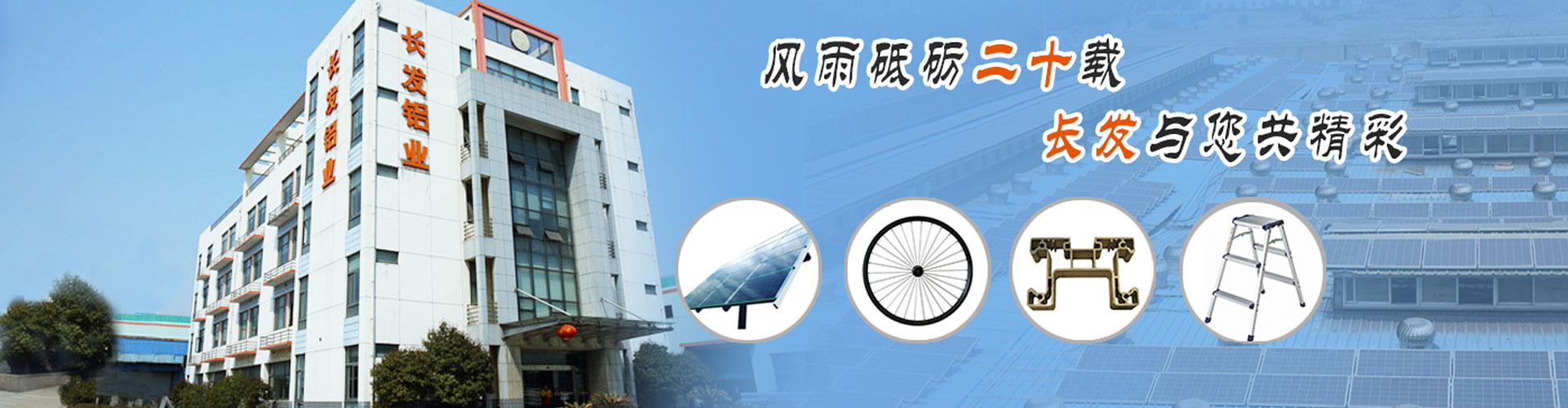王建:中國如何避免生產過剩危機
發布日期:2014-03-20 10:12 瀏覽量:1143
如果持續衰退是“滑落”,危機就是滑到崖邊后的“墜落”。在傳統市場經濟中,生產過剩危機的爆發,一般都要把增長率拉到“零”以下。中國既然還沒脫離傳統市場經濟,那就既可能爆發生產過剩危機,又可能會在危機中出現“負增長”。因此中國目前的經濟減速,不是進入了“中速增長期”,而是向增長的“斷崖”邊滑落。如果爆發危機,則在此之前一定會出現產能突然加速,或是需求突然萎縮,而這兩種情況目前都有前兆。
或向增長“斷崖”滑落
首先看產能,這可以用新增固定資產增長率來代表。2003-2007年產能增長率是22.1%,2008-2010年是24.3%,2011-2013年則是26.3%,即近三年是產能增長最快的時期。值得關注的是,代表未來投資需求增長率的新開工項目計劃總投資增長率,2012年還高達28.6%,去年就猛跌到只有14.2%,但代表產能增長的新增固定資產增長率仍高達22.5%,說明產能增長率超過了投資需求增長率8個百分點,而2008-2010年是投資需求超過產能增長6個百分點。這種產能突然超過投資增長的變化,就是爆發生產過剩危機的前兆。
其次看外需,如果有外部危機導致外需突然萎縮,也會引發國內的生產過剩危機,而新的國際金融危機正在醞釀,并很可能在明年爆發。從國際看,以美國和日本為代表的超級量寬政策,正在形成新的世界范圍內的資產泡沫,但其實體經濟復蘇乏力,因此又走回次貸危機爆發前依靠虛擬經濟繁榮的老路,所以正醞釀著下一場新的世界金融危機。去年下半年以來,美元指數持續走低,去年11月美國資本外流達300多億美元,12月更加劇到超過1100億美元。烏克蘭事件爆發后,國際資本不像以往那樣用美元資產避險,而是用日元和黃金避險,說明美國的金融市場已經進入了高危狀態,隨時可能爆發新危機。我估計這場新危機至遲會在明年下半年爆發,也不排除在今年爆發。而若新的金融危機再度來臨,中國外部需求就會再度發生顯著萎縮,出口需求可能突然萎縮,成為引爆中國生產過剩危機的重要原因。
第三看短期指標,經濟增長已有突然收縮動態。今年1月的貨幣M1增長率猛然收縮到只有1.3%的歷史最低水平。M1是交易中的貨幣,M1收縮說明貨幣正在大規模退出交易過程,這只會發生在企業的生產和投資活動大幅度收縮的時候。雖然今年以來M2的增速并不低,但M1才是交易中的貨幣,如果M2高速增長M1卻顯著萎縮,只能說明貨幣再寬松也已經對刺激經濟增長無效。另一個指標是出口,今年前兩個月出口負增長1.6%,其中2月當月負增長18.1%,這其中雖有去年同期出口虛高的影響,但自去年8月以來,PMI指數中的新出口訂單指數已連降7個月,說明當前出口的萎縮并不僅受去年基數影響。
還要注意,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一直是工業增長率顯著高于經濟增長率。1990年以后的23年里,工業增長率低于經濟增長率的年份只有兩個,一個是2009年,另一個就是2013年。2009年是因為次貸危機波及到中國,那去年是什么原因呢?只能說中國經濟中的內生增長動力開始收縮。那這種內生性收縮,會否使中國經濟增長從滑落轉向墜落?
所以,我認為中國目前已處在爆發生產過剩危機的前夜。今年可能還不是爆發危機的時候,但經濟增長會繼續減速到7%上下,下半年很有可能下行“破7”。明年則既有可能爆發國際金融危機,也有可能爆發國內生產過剩危機。
還需要警惕的是,金融危機有可能先于生產過剩危機爆發。在傳統市場經濟形態中,都是在經濟危機爆發后由于企業資金周轉不靈,才引出大量壞賬和金融危機。但是在二戰以前,甚至直到上世紀70年代以前,根本就沒有套利、期指、期權交易這些衍生金融工具,甚至連概念都沒有。但是中國的市場化是發生在世界資本主義主體邁入虛擬資本主義的時代,不可能不受到這些概念和工具的影響,甚至被當作金融市場的改革方向引入。
此外,美國爆發次貸危機的重要原因,就是實體經濟喪失競爭力后資本仍要牟利,當局放松金融管制,鼓勵金融創新,使虛擬經濟發展過頭,最終導致債務鏈條崩潰。反觀今天的中國,同樣存在因生產過剩而迫使產業資本外流到虛擬經濟領域牟利的格局。由于需要推動金融改革,各種機構在改革的名義下打著金融創新旗號瘋狂圈錢,以至于發展出超過4萬種理財產品,影子銀行的規模也從2007年前的6萬億元猛增到2012年的30萬億元。
但是實體經濟利潤增長停滯,已經撐不住虛擬經濟瘋狂發展。2007年以后,在各產業中真正能保持住利潤10%以上增長率的,只有房地產這一個產業。就是這一個產業,把國內產業資本、央行超發的貨幣乃至國際上的“熱錢”,都引到房地產融資這一個資產池中來。有分析認為,影子銀行的融資中至少有7成是圍繞房地產發生的。但先是前些年內地房價下跌,去年下半年以來沿海一線城市的樓市交易量也開始顯著萎縮,看來房地產這個資產泡沫也撐不住要破了,可能會引起金融危機先于產業危機而爆發。其中的機制與過程,與美國次貸危機的形成與爆發過程,是極為一致的。
中國如何避免危機
我認為,中國能避免危機,但所剩的時間已經不多。
首先,中國的過剩是物質產品生產能力的過剩,不像美國那樣是金融商品過剩,實物產品短缺。美國爆發金融危機的結果是那些金融商品沒銷路,不能再和發展中國家交換成物質產品,危機爆發后真會沒吃沒喝。但中國不同,即使爆發危機也不會因短了吃喝而要了命。而中國目前70%的設備利用率本身就說明,如果把利用率提升到90%這個正常水平,即使不用投資,生產仍然能增長20%。所以只要通過調整與改革開拓出內需通道,中國經濟就會重新煥發出增長生機。
其次,中國是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還有很大空間,因此過剩只是相對的,是因為分配不合理。如果能夠通過改革平衡好儲蓄、投資與消費的關系,就能繼續保持高增長。比如,雖然到去年中國鋼鐵產能達到10億噸,是中國過剩最嚴重的部門,但是人均鋼產量仍只有600公斤,而發達國家是人均1噸。中國未來20年人口可能還要增加1億,鋼鐵產能再增加5億噸都不夠。所以過剩永遠是相對的,是分配不好造成的。解決好了分配關系,過剩自然會消失。金融風險包括地方債的風險,也是因為實體經濟增長受到阻滯而產生的,實體經濟一旦有了出口,金融風險自然會化解。
最后,中國分配矛盾的特殊性不僅在于體制,更重要的是因為城鄉結構不合理,而城市化嚴重滯后是因為過去的發展政策不合理,這雖然是個嚴重問題,但也為今后的發展留出了巨大空間,即解決分配矛盾不僅靠體制改革,還得靠投資。因為沒有投資農民就進不了城,就沒地方住,沒地方就業,沒地方看病,子女也沒地方讀書。所以城市化過程就必然會帶來城市建設的巨大投入。我們以前進行的救市投資,只關注了用投資擴充當前需求,拉動當前增長,卻不管這些投資項目投產后產品到何處去。但若明確了城市化這個擴大內需的主要方向,再進行投資就不用顧慮投資后產能沒地方發揮,因為投資是為城市化服務的,是與未來增加消費緊密銜接的,再多也不嫌多。
糾正三個錯誤認識
沒有正確的認識就不可能有正確的行動,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是否把大規模城市化和以重構財政體系為目標,調整收入分配差距?在這個認識上如果不能統一,就只能浪費掉寶貴的調整和改革時間,坐等危機的來臨。不破不立,要統一認識,以下三個模糊不清的概念就必須糾正。
其一,認為只要充分發揮了市場作用,生產過剩矛盾就可以由市場自然解決,辦法就是繼續以推進市場化為主要改革取向,繼續向市場和企業放權。
中國自1979年以來30多年的改革,一直是在沿著向市場和企業放權的方向推進,當然到目前還有很多市場化不足的領域,但從總體看已經進入了全面市場化階段,基本標志就是已經出現嚴重生產過剩,而傳統經濟的基本特征則是短缺。這說明,阻礙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已經從政府與市場、企業的矛盾,轉變成企業與居民和居民之間在收入分配方面的矛盾,而這個問題是不能靠市場解決的。比如企業繼續搞活,產出增長利潤也增加,但老板會把錢拿出來給工人漲工資嗎?顯然不會。另外,政府不給農民工提供住房和社保,而僅僅給一個城市戶口,企業就會自動給農民工蓋房和買保險嗎?顯然也不會,所以就必須由政府來改革分配體制,建立與完善社保體系,以及大力推進城市化。
其二,認為凱恩斯主義僅僅是短期總量調節理論,因此把解決分配矛盾放到次要地位。
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的基本特征是生產過剩,而凱恩斯認為是“需求不足”,這都是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特征的描述。凱恩斯理論的重要繼承人之一、英國“新劍橋學派”的代表人物瓊·羅賓遜夫人的分析,更接近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方法,她認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中,工資與利潤是對立的,而這種對立來自于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料占有制,并導致了儲蓄與消費的失衡。這種“市場失靈”不可能由市場本身來糾正,而必須由政府插手分配來糾正。
社會總量平衡的長期特征,95%以上是由一個社會的制度安排所決定的,其他不足5%的部分才會隨短期宏觀政策安排而波動。從中國自己看,2009-2010年之間對市場的強烈宏觀刺激,也只是使一度下降到7%以下的經濟增長率又恢復到9%以上。但是當宏觀刺激政策退出,增長率就又掉到8%以下。這說明在今天的中國,不是宏觀需求政策不管用,而是制度安排所形成的儲蓄過剩不可能被短期的需求政策所改變。今年初以來M2的高增長率與M1的極低增長率并存,說明如果生產過剩迫使經濟進入下行通道,不觸動制度安排只提供寬松的貨幣,不能讓中國經濟增長走出低谷。有人說經濟中的短期問題都是總量與需求問題,長期問題都是供給和結構問題,這恐怕有些絕對。因為總量平衡關系首先取決于制度安排,而制度安排是長期問題。只有在制度安排合理的時候發生了不好的長期增長趨勢,才應該懷疑是供給結構出了問題。
其三,認為中國的消費并不低,調整分配與增加消費,包括讓大批農民進城,都會損害經濟增長。
認為消費并不低的依據是,2008年以來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按現價計算,年增長率已高達16.8%,比同期的現價GDP增長率還高。但儲蓄和投資是經濟增長的源泉,因此鼓勵消費就是消耗掉增長的后勁。
消費高和低,主要是看比例。新千年以來中國居民消費率不斷降低是個不爭的事實,如果看增速則是個說不清的事。比如,“九五”到“十五”這十年,投資、消費加按人民幣計價的出口,與現價GDP總值差不多,但到“十一五”期間卻高出27.4%,去年更高出44.5%。按理說投資、消費加出口是從需求端統計的GDP,應該和從生產端統計出的GDP數據差不多。雖然固定資產投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和人民幣出口值,與支出法統計中的口徑有差距,但為什么以前差不多,現在卻差了這么多?只能說統計口徑和范圍可能發生了變化,因此僅僅用消費增長高于GDP來說明中國居民消費并不低,已經不行了,還是要看消費相對于投資的增長,或者是消費率的變化,才能更接近事實。要是這么看,2008年以來投資的增長率是25%,比消費增長率年均高出8個百分點,消費在收入分配中的比率怎么能不降。
不是投資和消費占比高就好,而是要保持恰當的比例,才會實現最好的發展增速與經濟效益。目前的矛盾是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導致嚴重生產過剩,所以必須通過推進城市化和調整分配關系來開啟內需。
最后要說的是,如果不能至遲在今年下半年推出龐大的城市化投資計劃,寶貴的調整機遇就可能喪失。當經濟增長真的掉下“斷崖”,恐怕推什么都為時已晚了,所以必須盡快統一認識,行動起來。至于對分配體制的調整,則可以放到經濟增長開始反彈之后,再來安排。
或向增長“斷崖”滑落
首先看產能,這可以用新增固定資產增長率來代表。2003-2007年產能增長率是22.1%,2008-2010年是24.3%,2011-2013年則是26.3%,即近三年是產能增長最快的時期。值得關注的是,代表未來投資需求增長率的新開工項目計劃總投資增長率,2012年還高達28.6%,去年就猛跌到只有14.2%,但代表產能增長的新增固定資產增長率仍高達22.5%,說明產能增長率超過了投資需求增長率8個百分點,而2008-2010年是投資需求超過產能增長6個百分點。這種產能突然超過投資增長的變化,就是爆發生產過剩危機的前兆。
其次看外需,如果有外部危機導致外需突然萎縮,也會引發國內的生產過剩危機,而新的國際金融危機正在醞釀,并很可能在明年爆發。從國際看,以美國和日本為代表的超級量寬政策,正在形成新的世界范圍內的資產泡沫,但其實體經濟復蘇乏力,因此又走回次貸危機爆發前依靠虛擬經濟繁榮的老路,所以正醞釀著下一場新的世界金融危機。去年下半年以來,美元指數持續走低,去年11月美國資本外流達300多億美元,12月更加劇到超過1100億美元。烏克蘭事件爆發后,國際資本不像以往那樣用美元資產避險,而是用日元和黃金避險,說明美國的金融市場已經進入了高危狀態,隨時可能爆發新危機。我估計這場新危機至遲會在明年下半年爆發,也不排除在今年爆發。而若新的金融危機再度來臨,中國外部需求就會再度發生顯著萎縮,出口需求可能突然萎縮,成為引爆中國生產過剩危機的重要原因。
第三看短期指標,經濟增長已有突然收縮動態。今年1月的貨幣M1增長率猛然收縮到只有1.3%的歷史最低水平。M1是交易中的貨幣,M1收縮說明貨幣正在大規模退出交易過程,這只會發生在企業的生產和投資活動大幅度收縮的時候。雖然今年以來M2的增速并不低,但M1才是交易中的貨幣,如果M2高速增長M1卻顯著萎縮,只能說明貨幣再寬松也已經對刺激經濟增長無效。另一個指標是出口,今年前兩個月出口負增長1.6%,其中2月當月負增長18.1%,這其中雖有去年同期出口虛高的影響,但自去年8月以來,PMI指數中的新出口訂單指數已連降7個月,說明當前出口的萎縮并不僅受去年基數影響。
還要注意,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一直是工業增長率顯著高于經濟增長率。1990年以后的23年里,工業增長率低于經濟增長率的年份只有兩個,一個是2009年,另一個就是2013年。2009年是因為次貸危機波及到中國,那去年是什么原因呢?只能說中國經濟中的內生增長動力開始收縮。那這種內生性收縮,會否使中國經濟增長從滑落轉向墜落?
所以,我認為中國目前已處在爆發生產過剩危機的前夜。今年可能還不是爆發危機的時候,但經濟增長會繼續減速到7%上下,下半年很有可能下行“破7”。明年則既有可能爆發國際金融危機,也有可能爆發國內生產過剩危機。
還需要警惕的是,金融危機有可能先于生產過剩危機爆發。在傳統市場經濟形態中,都是在經濟危機爆發后由于企業資金周轉不靈,才引出大量壞賬和金融危機。但是在二戰以前,甚至直到上世紀70年代以前,根本就沒有套利、期指、期權交易這些衍生金融工具,甚至連概念都沒有。但是中國的市場化是發生在世界資本主義主體邁入虛擬資本主義的時代,不可能不受到這些概念和工具的影響,甚至被當作金融市場的改革方向引入。
此外,美國爆發次貸危機的重要原因,就是實體經濟喪失競爭力后資本仍要牟利,當局放松金融管制,鼓勵金融創新,使虛擬經濟發展過頭,最終導致債務鏈條崩潰。反觀今天的中國,同樣存在因生產過剩而迫使產業資本外流到虛擬經濟領域牟利的格局。由于需要推動金融改革,各種機構在改革的名義下打著金融創新旗號瘋狂圈錢,以至于發展出超過4萬種理財產品,影子銀行的規模也從2007年前的6萬億元猛增到2012年的30萬億元。
但是實體經濟利潤增長停滯,已經撐不住虛擬經濟瘋狂發展。2007年以后,在各產業中真正能保持住利潤10%以上增長率的,只有房地產這一個產業。就是這一個產業,把國內產業資本、央行超發的貨幣乃至國際上的“熱錢”,都引到房地產融資這一個資產池中來。有分析認為,影子銀行的融資中至少有7成是圍繞房地產發生的。但先是前些年內地房價下跌,去年下半年以來沿海一線城市的樓市交易量也開始顯著萎縮,看來房地產這個資產泡沫也撐不住要破了,可能會引起金融危機先于產業危機而爆發。其中的機制與過程,與美國次貸危機的形成與爆發過程,是極為一致的。
中國如何避免危機
我認為,中國能避免危機,但所剩的時間已經不多。
首先,中國的過剩是物質產品生產能力的過剩,不像美國那樣是金融商品過剩,實物產品短缺。美國爆發金融危機的結果是那些金融商品沒銷路,不能再和發展中國家交換成物質產品,危機爆發后真會沒吃沒喝。但中國不同,即使爆發危機也不會因短了吃喝而要了命。而中國目前70%的設備利用率本身就說明,如果把利用率提升到90%這個正常水平,即使不用投資,生產仍然能增長20%。所以只要通過調整與改革開拓出內需通道,中國經濟就會重新煥發出增長生機。
其次,中國是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還有很大空間,因此過剩只是相對的,是因為分配不合理。如果能夠通過改革平衡好儲蓄、投資與消費的關系,就能繼續保持高增長。比如,雖然到去年中國鋼鐵產能達到10億噸,是中國過剩最嚴重的部門,但是人均鋼產量仍只有600公斤,而發達國家是人均1噸。中國未來20年人口可能還要增加1億,鋼鐵產能再增加5億噸都不夠。所以過剩永遠是相對的,是分配不好造成的。解決好了分配關系,過剩自然會消失。金融風險包括地方債的風險,也是因為實體經濟增長受到阻滯而產生的,實體經濟一旦有了出口,金融風險自然會化解。
最后,中國分配矛盾的特殊性不僅在于體制,更重要的是因為城鄉結構不合理,而城市化嚴重滯后是因為過去的發展政策不合理,這雖然是個嚴重問題,但也為今后的發展留出了巨大空間,即解決分配矛盾不僅靠體制改革,還得靠投資。因為沒有投資農民就進不了城,就沒地方住,沒地方就業,沒地方看病,子女也沒地方讀書。所以城市化過程就必然會帶來城市建設的巨大投入。我們以前進行的救市投資,只關注了用投資擴充當前需求,拉動當前增長,卻不管這些投資項目投產后產品到何處去。但若明確了城市化這個擴大內需的主要方向,再進行投資就不用顧慮投資后產能沒地方發揮,因為投資是為城市化服務的,是與未來增加消費緊密銜接的,再多也不嫌多。
糾正三個錯誤認識
沒有正確的認識就不可能有正確的行動,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是否把大規模城市化和以重構財政體系為目標,調整收入分配差距?在這個認識上如果不能統一,就只能浪費掉寶貴的調整和改革時間,坐等危機的來臨。不破不立,要統一認識,以下三個模糊不清的概念就必須糾正。
其一,認為只要充分發揮了市場作用,生產過剩矛盾就可以由市場自然解決,辦法就是繼續以推進市場化為主要改革取向,繼續向市場和企業放權。
中國自1979年以來30多年的改革,一直是在沿著向市場和企業放權的方向推進,當然到目前還有很多市場化不足的領域,但從總體看已經進入了全面市場化階段,基本標志就是已經出現嚴重生產過剩,而傳統經濟的基本特征則是短缺。這說明,阻礙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已經從政府與市場、企業的矛盾,轉變成企業與居民和居民之間在收入分配方面的矛盾,而這個問題是不能靠市場解決的。比如企業繼續搞活,產出增長利潤也增加,但老板會把錢拿出來給工人漲工資嗎?顯然不會。另外,政府不給農民工提供住房和社保,而僅僅給一個城市戶口,企業就會自動給農民工蓋房和買保險嗎?顯然也不會,所以就必須由政府來改革分配體制,建立與完善社保體系,以及大力推進城市化。
其二,認為凱恩斯主義僅僅是短期總量調節理論,因此把解決分配矛盾放到次要地位。
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的基本特征是生產過剩,而凱恩斯認為是“需求不足”,這都是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特征的描述。凱恩斯理論的重要繼承人之一、英國“新劍橋學派”的代表人物瓊·羅賓遜夫人的分析,更接近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方法,她認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中,工資與利潤是對立的,而這種對立來自于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料占有制,并導致了儲蓄與消費的失衡。這種“市場失靈”不可能由市場本身來糾正,而必須由政府插手分配來糾正。
社會總量平衡的長期特征,95%以上是由一個社會的制度安排所決定的,其他不足5%的部分才會隨短期宏觀政策安排而波動。從中國自己看,2009-2010年之間對市場的強烈宏觀刺激,也只是使一度下降到7%以下的經濟增長率又恢復到9%以上。但是當宏觀刺激政策退出,增長率就又掉到8%以下。這說明在今天的中國,不是宏觀需求政策不管用,而是制度安排所形成的儲蓄過剩不可能被短期的需求政策所改變。今年初以來M2的高增長率與M1的極低增長率并存,說明如果生產過剩迫使經濟進入下行通道,不觸動制度安排只提供寬松的貨幣,不能讓中國經濟增長走出低谷。有人說經濟中的短期問題都是總量與需求問題,長期問題都是供給和結構問題,這恐怕有些絕對。因為總量平衡關系首先取決于制度安排,而制度安排是長期問題。只有在制度安排合理的時候發生了不好的長期增長趨勢,才應該懷疑是供給結構出了問題。
其三,認為中國的消費并不低,調整分配與增加消費,包括讓大批農民進城,都會損害經濟增長。
認為消費并不低的依據是,2008年以來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按現價計算,年增長率已高達16.8%,比同期的現價GDP增長率還高。但儲蓄和投資是經濟增長的源泉,因此鼓勵消費就是消耗掉增長的后勁。
消費高和低,主要是看比例。新千年以來中國居民消費率不斷降低是個不爭的事實,如果看增速則是個說不清的事。比如,“九五”到“十五”這十年,投資、消費加按人民幣計價的出口,與現價GDP總值差不多,但到“十一五”期間卻高出27.4%,去年更高出44.5%。按理說投資、消費加出口是從需求端統計的GDP,應該和從生產端統計出的GDP數據差不多。雖然固定資產投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和人民幣出口值,與支出法統計中的口徑有差距,但為什么以前差不多,現在卻差了這么多?只能說統計口徑和范圍可能發生了變化,因此僅僅用消費增長高于GDP來說明中國居民消費并不低,已經不行了,還是要看消費相對于投資的增長,或者是消費率的變化,才能更接近事實。要是這么看,2008年以來投資的增長率是25%,比消費增長率年均高出8個百分點,消費在收入分配中的比率怎么能不降。
不是投資和消費占比高就好,而是要保持恰當的比例,才會實現最好的發展增速與經濟效益。目前的矛盾是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導致嚴重生產過剩,所以必須通過推進城市化和調整分配關系來開啟內需。
最后要說的是,如果不能至遲在今年下半年推出龐大的城市化投資計劃,寶貴的調整機遇就可能喪失。當經濟增長真的掉下“斷崖”,恐怕推什么都為時已晚了,所以必須盡快統一認識,行動起來。至于對分配體制的調整,則可以放到經濟增長開始反彈之后,再來安排。
上一篇:這才是工廠質量管理的最高境界!
下一篇:多重因素壓制 鋁價仍存下行風險
聯系我們
- 郵箱:sales@www.pixalbum.net
- 電話:0512-52481273/52136111
- 傳真:0512-52480998/52480997
- 地址:常熟市辛莊臺資工業園區
版權所有: 常熟市長發鋁業有限公司 蘇ICP備19049930號-1

 服務熱線:
服務熱線: